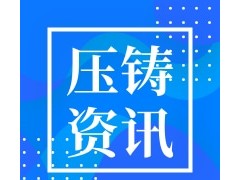柳叶形剑身、鱼形剑柄、螺旋形剑柄……四把造型独特的青铜剑吸引着参观者的目光。
这四把剑分别叫战国鱼形柄剑、战国鱼形柄青铜剑、战国螺旋柄乳钉纹山字格青铜剑和战国螺旋柄山字格青铜剑。
四把古剑出自宝兴
“这四把剑都出土于宝兴县。”市文管所所长李炳中说。
1978年,在宝兴县五龙乡瓦西沟,发现一处石棺墓葬,里面的两把鱼形柄剑,吸引了市文管所和宝兴县文管所的注意。
两把剑都是青铜剑,尖峰、双刃,其中一把长度32厘米的被评为一级文物,另一把长31.5厘米的被评为二级文物。
1980年,在宝兴县明礼乡干溪土坑墓,出土一把战国螺旋柄乳钉纹山字格青铜剑。1989年,宝兴县又出土了一把战国螺旋柄山字格青铜剑,均为二级文物。
1990年春,在宝兴县城西北约二十余公里的陇东乡汉塔山发现了一处战国土坑积石墓葬群,里面又发现了一些鱼形柄剑和山字格剑。
李柄中说:“鱼形柄剑和山字格剑都是反映当地羌族文化的重要凭证。”
这些鱼形柄剑和山字格剑为何频频现于宝兴,它们有何用途,它们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羌族勇士的佩剑与利器
尖峰,柳叶剑形,圆形隆脊,援身微束,双弧刃,柄弯曲向后渐束,呈鱼形,椭圆形柄首……是鱼形柄剑的特点。
而山字格剑的剑身呈柳叶形,双刃,双面隆脊,柄饰螺旋纹和双行乳钉纹,中空,柄首椭圆,且有两穿孔通向中空柄……
“根据专家考证,这些剑为战国时期西南夷民族所用的剑。”李炳中说。
几把古剑,藏于市博物馆内,虽然剑身已有斑斑铜绿,但锋利的剑锋,仍寒气逼人。那双刃上下局部锈蚀的齿缺,仿佛向来者诉说着一个个久远的故事。
立于古剑前,2000多年前的一场战斗仿佛就在眼前显前。
2000多年前的一天,在中国西部,一队身着羌服的勇士手握鱼形柄剑,骑着骏马,驰骋在高原的原野上,与另一队人马厮杀。
战斗的结果无人知晓,但这些剑被保存了下来。
“这些剑的用途除了当地人作为武器外,还是羌族勇士勇武的象征。”宝兴县文管所所长宋甘文说,“春秋时期,生活在现四川青衣江一带的古羌族游牧民族骁勇好斗,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战斗。鱼形柄剑和山字格剑便是古羌族人民发明并使用的一种战斗武器,同时,佩带宝剑也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西南夷文化发展的明证
“这些剑展示着巴蜀文化对于西南夷地区的影响。”李炳中说。
巴蜀文化是巴人和蜀人后期的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7世纪到前2世纪。在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两国以后,整个川西高原山地当时被称为“西南夷”。
川西高原青铜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以石棺葬为特征,这是一种用石板或石块垒砌的石棺。此外还盛行山字格青铜剑。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宝兴县频频发现石棺葬,并在石棺葬内发现巴蜀青铜器和反映当地文化的鱼形柄剑及山字格剑。
“在宝兴县出土的文物中,巴蜀文化和羌族文化在同一墓葬群中相互碰撞和融合,恰恰反映了两个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宋甘文说。
这一地区的文化进入青铜器时代的年代大体在公元前8世纪以后。在西汉中期(前2—前1世纪)汉帝国的势力进入这一地区之后,土著文化迅速衰败,到西汉晚期时已经基本趋于消失。
“鱼形柄剑和山字格剑,对于研究西南夷文化,提供了充分的实物证明。”李炳中说。
青铜剑铸造之谜
锋利的剑刃、精美的剑身,展现着古剑铸造的技艺。
经考古人员研究,鱼形柄剑和山字格剑的铸造工艺在当时算是一流。
那么,当时的西南夷是否拥有了先进的铸造工艺?
宋甘文查阅相关史料得知,在历史上,宝兴县的大山内一度盛产铁矿和铜矿。这些剑是否是当地人所铸造?
宋甘文一直努力找寻有关线索,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在宝兴县境内发现同时代铸造兵器的遗址。”
“这些剑有可能是在其它地方铸造的。”宋甘文说,西南夷地区包括了川西高原的大部分地区,盛产铁矿和铜矿的宝兴县,为西南夷的勇士提供了铸造兵器的原料。
“他们的铸造技术,受着当时巴蜀文化的影响,但又呈现出自己的特点。”对于剑的铸造技术之谜,李炳中分析。“巴蜀文化与西南夷文化的交流,让西南夷也掌握了先进的铸造技术,从而形成了西南夷独特的兵器文化。”
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同民族都在不断地发展,“鱼形柄剑和山字格剑,从一个侧面反映着当时西南夷地区的文化进程。”李炳中说。
记者黄伟严玉琳

鱼形柄剑

山字格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