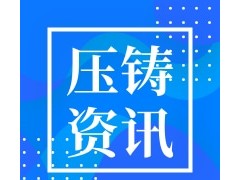“现在工厂的产能下降了三分之一,工厂订单减少了30%。”10月15日,江苏省常州市常顺铸造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志伟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焦虑地说。
美的实习业务员之死:企业肉搏演变为员工肉搏 十二五规划十大重点
统计局:民众生活富裕程度下降 美国曝5000亿美元买债计划 周小川:通胀等风险将显著上升 蒙牛就诽谤伊利致歉 自曝旧案 广东黑老大判死 曾被用来吓小孩 巴曙松:台湾企业家最爱什么话题 此时,焦虑的不仅仅是常顺铸造一家企业。自从整个常州市8月25日正式出台了《2010年市区工业企业节能应急用电调控方案》以来,很多企业都面临产能下降、订单减少等问题。
常州市出台的用电调控方案包括:对化工等连续生产企业执行“开二周停一周”的集中轮休方案;对冶金用电大户执行用电总量控制方案;对其他企业按供电线路分成14组,采取“开九天停五天”的线路轮休方案。常顺铸造属于第三类,被分在了第14组。
在限电面前,常顺铸造不得不让工人在供电期间完成更多的工作。
“目前,我们原先承接的部分订单无法完成,就跟客户解释。还好客户都是国内客户,跟他们解释是因为限电导致不能如期交货,他们也还理解,就将订单转移到其他一些没有实施限电政策的省份了。”朱志伟说。
让朱志伟担心的不仅是因为限电会带来订单的减少,还有工人的流失。
常顺铸造采取计件工资,现在限产,工人的收入明显下降。“现在限电企业的成本已经很高了,我们本来就属于薄利经营,还按正常生产量支付员工工资,企业也承担不起。”朱志伟说,“常州铸造的工人60%来自外地,为了避免工人利用5天休假时间回家不来了,我们就向政府申请生产5天,休息2天。但是总体的电量是一定的,只能就生产时间作出调整。”
亟待法律规范
拉闸限电、限产停产,在各地冲刺节能减排目标中无疑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然而,这种带有浓厚强制性色彩的措施能否真正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持续推动节能减排目标的完成,业界多持否定看法。
在中国人民大学行政法学教授杨建顺看来,一些地方政府在实现节能减排上有点本末倒置,将本应该作为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节能减排手段当作了目标。这种强制性的节能减排措施在完成“十一五”阶段的冲刺后,如果不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从调整产业结构的角度入手,各地的节能减排效果极有可能出现反弹。而且在限电过程中,一些小企业利用自备的柴油发电机等发电设备提供电力,保持企业的正常运转,这种方式虽然不影响国家对地方节能指标的完成,但是对环境可能造成更大的破坏作用。
[nextpage]
美的实习业务员之死:企业肉搏演变为员工肉搏 十二五规划十大重点
统计局:民众生活富裕程度下降 美国曝5000亿美元买债计划 周小川:通胀等风险将显著上升 蒙牛就诽谤伊利致歉 自曝旧案 广东黑老大判死 曾被用来吓小孩 巴曙松:台湾企业家最爱什么话题 各地为完成节能减排任务,采取一刀切的“拉闸限电”行为,杨建顺说:“有违法的嫌疑。政府在采取拉闸限电行为时,如果没有对居民进行充分告知,对居民造成的损失要承担赔偿责任。对不在调整范围内的企业采取一刀切的行为造成的损失也应当予以补偿。”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能源法专家肖国兴在此前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拉闸限电’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相反有其必然性。不需要支付谈判成本,政府单凭命令就能直接剥夺用户或消费者对能源的消费,且具有规模效应,对节能降耗指标的实现能立竿见影。和调整产业结构与能源结构相比,‘拉闸限电’更具有行政效率”。
一方面是各地政府为了达成目标采取“一刀切”的限电限产突击行为,一方面又是一些地方政府先前没有严格执行国家的调控政策,而是出于地方经济增长的需要,对高污染、高耗能企业采取保护措施。
据了解,早在2007年,国家发改委先后还出台一系列电价调控政策,比如,2007年取消电解铝行业电价优惠,对八类“两高”企业实施差别电价政策,然而这些政策也并没有落实到位。约有一半的省市自治区没有执行,一些省份还推出了优惠电价。对此,杨建顺认为,如果地方政府对国家规定的必须关停的高污染企业没有采取关停措施,而让其继续生产的话,作为公民,可以就高污染企业对其生产生活造成的损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行使危害排除请求权,人民法院应当保障公民的诉权。
杨建顺解释,对于节能减排,政府应当将目标管理同手段管理结合起来。对政府节能减排所应采取的手段、办法、途径都予以明确规定,这样可以避免一些地方政府采取“拉闸限电”等非常规手段。同时还应该加强监督制约机制的建立。这包括相关部门进行定期、不定期的监督检查,还包括公民“危害排除请求权”的顺利行使。
需引入市场机制
有专家认为,对于节能减排来说,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加大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小企业的关停力度,加快淘汰落后的生产力。
自2005年推行节能减排以来,中央政府曾对各个高耗能产业出台了行业准入条件,要求各个行业以准入条件为依据,进行项目核准。然而,由于地方政府出于GDP增长的考虑,对一些达不到准入条件的企业,采取了默许的态度,甚至对一些纳税大户的高耗能高污染企业,通过红头文件等措施予以保护。而此前被寄予厚望的差别电价,在实施过程中,因一些地方政府不作为导致收效甚微。“这就导致地方政府在节能减排上,前期欠账太多,以至于后期采取‘一刀切’的限电限产方式。”杨建顺说。
然而,中央和地方利益很难在该问题上达成一致。不改变“GDP”政绩观,地方政府在推进节能减排工作过程中就缺乏足够的动力,容易导致地方政府的不作为。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才能使节能减排成为政府、企业的主动选择,而非被动应付。
对此,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钟茂初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说,各级部门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目标必须与“节能减排”目标相匹配。要先确定“节能减排”的强制性约束目标,在此硬约束条件下再去确立经济增长率、投资增长率、消费增长率、出口增长率以及产业结构、城市化率等各种发展指标。这个顺序不能颠倒,否则,“节能减排”目标就必然成为软约束。
李长安建议,政府要充分利用税收政策和金融政策增加“两高”(高耗能、高污染)行业企业的生产成本,比如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污染和产能过剩行业企业贷款,而对从事环保研发的企业,则可以采取简化贷款手续、并给予一定的利率优惠措施予以支持。这样的安排则有助于促使企业主动作出选择,逐步退出“两高”行业和项目。
同时,李长安还建议,国家应大力发展排污权转让市场,这样不仅有利于国家控制总量,而且也使企业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节能减排成本,主动采取节能降耗措施。